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社区。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立即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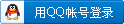
×

地基:反应堆将坐落在493 根基柱上,基柱顶端还加盖了钢和橡胶构成的减震器,以保证重达40 万吨的整个结构不受地表震动的影响。 世界上最复杂的实验遭遇坎坷,通往终极能源之路何日坦平?
撰文 杰夫·布鲁姆菲尔(Geoff Brumfiel) 翻译 庞玮
1985年11月,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日内瓦时,那里的天气阴沉而寒冷。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到此是为了会晤苏联新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里根认为,当时世界面临核战浩劫的风险很高,于是想缩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渐膨胀的军备库,而戈尔巴乔夫同样也意识到军备竞赛正在拖垮苏联的经济。
但是,双边会谈很快陷入僵局。里根在苏联历次入侵别国的问题上指责戈尔巴乔夫,而戈尔巴乔夫则抓住星球大战计划,一个试图将所有来袭核弹头拦截在外太空的野心计划,来反击里根。会晤濒于破裂。到清晨5点,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包含任何实际承诺的联合声明,在声明的最后,几乎是脚注的位置,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加入了一个含糊不清的保证,即两国将“本着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开发一种新能源。
上述脚注最终付诸实际,成为一个项目,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演变成可谓是21世纪人类最宏大的科学活动,一场复杂实验技术的“交响乐”。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能源危机。这就是ITER(International Thermonuclear Experimental Reactor),全称“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它要在地球上制造出太阳,消耗50兆瓦的能量,却会输出10倍于此、达到500兆瓦的动力,所需要的仅仅是宇宙中最丰富的物质:氢。该项目将着眼于原理论证,希望最终描绘出的技术,能填满人类对能源的无尽索求。各个项目参与国的政治家对推动该项目的热情一直不减。
但正如催生出该项目的首脑会谈一样,ITER也不孚众望。预算已经翻倍再翻倍,工程技术上的问题又总是被一再敷衍。一些技术流程也很繁琐,比如参与国不是集中资源一同开发,而是先在各自国家生产零零碎碎的组件,再运到法国南部ITER所在地去组装。整个过程好比一个人先从网上订购一堆螺母、螺栓和支架,然后试图在后院捣鼓出一架波音747客机来。结果自然如冰上行舟,将近一年前ITER还只是地上一个10多米深的大洞,直到最近才刚刚把约100多万立方米的混凝土填下去。项目投入运行的日期也从2016年推至2018年,再推至2020年底。首次净能量输出实验起码要等到2026年,此时距项目开工已20年。
即便如此,ITER还只是这种公认新能源的序幕,就算ITER获得成功,之后还要建造第二代的测试反应堆,只有这些反应堆都运行正常,各地才会建造能够并网发电的核聚变电站。ITER只是第一步,整个计划将为期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该项目的支持者提出,从长远来看,为了满足世界对能源的持续需求,ITER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但即便是这些支持者,也不得不打消对ITER乌托邦式的期望。目前看起来,该项目只是靠制度惯性维持着,毕竟对各国政府而言,做一个一成不变的参与者总比成为众矢之的的退出者要容易些。另一方面,该项目的每一次延期和预算超支都为批评者提供了更多的攻击靶子,他们形容ITER是一个浪费钱的怪兽,吃掉了眼下很多其他能源研究项目所急需的经费。两派虽各有坚持,但有一条却是双方的共识,那就是如果最后选择了ITER,它最好成功,千万不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瓶中烈日
理论上,核聚变是最完美的能源。它建立在一个几乎人所共知的物理原理之上: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由于光速很大,所以该公式意味着只需要非常小的一点质量就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所有的核反应都基于上面这条宇宙基本法则,在常见的核电站中,比较重的铀原子核分裂成更轻的原子核,在此裂变(fission)过程中,铀原子核有很小一部分质量直接变成能量。聚变(fusion)过程基于同样的原理,但过程刚好与裂变相反,轻原子核比如氢核发生碰撞,产生氦核,而氦核的质量要略小于参与碰撞的氢核质量之和,消失的那部分质量就直接变成了能量。就单位质量而言,聚变燃料可以释放出三倍于铀裂变的能量,更重要的是,氢的贮量要远比铀丰富,而且聚变产生的氦废料没有辐射污染之虞。
“ 聚变让人着迷,”为ITER协调奔走多年的韩国科学家李秀景(Gyung-SuLee)说,“它就像中世纪的人们追寻的炼金术一般,它是能源研究的‘圣杯’。”李秀景是聚变能源的积极拥护者。1980年,他来到美国,成为芝加哥大学的一名研究生,专攻量子场论这一物理学中的硬骨头。但是美国改变了他的想法,“在美国,金钱就是一切,”他回忆道,而量子场论只能带来思想上的收获。于是,他开始寻找一个更实用的学习目标,最后选择了聚变,因为“聚变兼具科学和工程上的挑战性”。而且聚变美梦一旦成真,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能量会唾手可得、轻贱如土,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将变得无关紧要,世界将为之转变。
像李秀景这样的科学家已经为聚变神魂颠倒了半个世纪。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都宣称黎明即将来临,其中有些的确是哗众取宠之辈,更多的人不过是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聚变桀骜难驯,自然一次次斩断了人类的梦想。
最主要的困难来自这个“聚”字,因为氢离子会相互排斥,所以科学家必须将它们紧压在一起,产生聚变。ITER的策略是在一个磁场囚笼中加热氢原子,它采用的磁场囚笼形式被称为托卡马克(tokamak),外形就是一个面包圈形的金属环上缠绕着一匝匝线圈。这些线圈用来产生磁场,当由氢离子构成的带电等离子体被加热至数十亿度时,磁场负责将它们紧紧地约束在一起,因为这个温度能气化任何固体材料,只有用磁场来做容器。
在20世纪70年代,托卡马克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有些研究者甚至预言,到20世纪90年代就能建造出聚变核电站来。当时唯一的挑战就是,如何把研究型反应堆放大到实用尺寸,一般而言,托卡马克结构越大,其中的等离子体能达到的温度就越高,核聚变的效率也就越高。
然而问题渐起。等离子体内部能传导电流,受自激电流的影响,等离子体会变得弯拱扭曲,形成剧烈的乱流,这些乱流像鞭子一样抽打等离子体,将其甩出磁笼,冲击装置的外壁。于是,随着等离子体温度升高,必须要有更大的托卡马克来提供额外的空间,同时还要有更强的磁场来约束等离子体。这两者都需要增大线圈中的电流,而更大的电流意味着更高的能耗,结果很清楚:托卡马克越大越强,它就需要更多的能量来维持。
这种正反馈意味着,普通的托卡马克装置永远也无法输出净能量。对此,包括李秀景在内的研究者只知道一种招架方法:超导,即利用有些导体在很低温度下电阻消失因而没有电能损耗的特性。如果托卡马克的电磁铁使用超导材料,只需注入一次电流,它就会一劳永逸地运转下去。这样能耗虽然降低了,但花费却非常巨大,超导体是一种特殊、昂贵的材料,而且为了维持超导状态,必须用液氦一直冷却它们,使之处于非常接近绝对零度的状态。
基于上述原因,早在1985年形势就非常明了,那就是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无法建造能并网发电的大型托卡马克装置。因此,ITER项目正式开始之初就是一个由美国、苏联、日本和
欧洲共同参与的联合项目。整个项目设计非常庞大,用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除了超导体之外,ITER还通过高级加速器注入中性原子束来加热核心装置,并有一系列复杂的天线像微波炉那样来加热等离子体。ITER没有用普通的氢来充当燃料,而采用了氘和氚,它们是氢的两种同位素,与氢相比它们聚变所需的温度和压力更低。氘在自然界中相对常见,一滴海水中就含有数万亿个氘原子,但有放射性的氚则极为罕见,因而价格不菲。最初估计ITER的建造费用约为50亿美元,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对装置的复杂程度进行更为详细的评估之后,预算翻倍了。1998年,主要基于对开支的考虑,美国退出了该项目。
就在美国退出后不久,一个受命拯救该项目的小组匆匆忙忙对其进行了重新设计,将装置尺寸和预算都缩减到了原来的一半。不幸的是,“由于太赶时间,重新设计时在考虑上有所欠缺,”ITER的资深科学家,同时也是最初那个设计小组的成员京特· 詹施茨(Gunther Janeschitz)说。参与国都在争抢装置中大部件的设计建造任务,而像引线、连接件这样的小东西却无人问津。詹施茨举了个例子,“在两个部件之间本来应该有连接孔的,但没有哪份采购标书具体指出了这一点”
这些沟通上的鸿沟正是ITER的苦难之源,因为ITER组织本身并不负责该装置的实际制造。先期参与国如俄罗斯和日本,希望自己的投入能为本国相关实验室的科学家所用,而印度这样的新加入国,则想学习新的高端技术,发展自己的工业。因此,成员国提供的都是制作完成的部件(附带提供一小笔经费给统筹机构),电磁铁所用的超导线缆来自日本东芝公司,但同时中国西部超导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俄罗斯叶夫列莫夫电物理设备研究院也提此类线缆;装置所用的巨大真空室将在欧洲、印度、韩国和俄罗斯建造;加热系统则来自欧洲、日本和美国——美国于2003年重新加入了ITER项目。ITER的统筹机构需要接收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这些部件,补齐尚缺少的部件,然后把所有东西拼装成迄今为止最复杂的实验装置。
与ITER临时总部相隔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就是郎司河(Durance River),河边有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可以俯览流水。在这座城堡中,清楚地展现出ITER所面临的挑战:ITER的成员聚集于此,挤在一间特意建造的会议室中,周围布满了液晶显示屏和麦克风,正在召开的是一次协调会,而与会者无意让我这个记者参与其中。不过在中场休息时,李秀景向我透露了会议室中上演的一场小纷争。“印度人认为一条管道应该在这里截止,而其他人则认为该在那里截止,”他边说边从桌上拿起一小条巧克力棒,朝着房间的另一端指了指,“最简单的解决方案是在中间截止,但技术上做不到,于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交由总干事裁决。”
截止到2010年,ITER的总干事都是由一个让人昏昏欲睡的日本外交官池田要(Kaname Ikeda)担任。由于处理此类管道之争乏力,池田在ITER委员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由日本核聚变科学家本岛修(Osamu Motojima)接任,后者是ITER的资深人员,在平和的外表之下有着坚毅、果决的性格。来自欧洲和美国子项目的一些资深人员则充任本岛的副手,最终他们与印度人在紧挨着会议室的一个改建而成的套间里达成了协议。就在这些人争论不休时,当时还是ITER首席法律顾问的哈里·图伊德(Harry Tuinde,之后他就离开了ITER去为欧洲议会工作了)坐在院子里抽着雪茄。我问他,如果本岛有权力要求各参与国提供指定部件,事情会不会顺利很多?图伊德往椅背上一靠,“那基本上就把你竭力要维持的关系都弄糟了”。 归根结底,维系这个项目的不是ITER总干事的权威,而是成员参与的意愿。
通向能源之路
就在沟通磕磕绊绊地进行之时,ITER的经费预算已经再次加倍,达到200亿美元,这只是明面上的金额,由于采用了散件组装的方式来建造,实际建造费用很难统计。项目的完成日期也再次向后推迟了几年。
不断攀升的成本和日复一日的拖延,让反对巨型托卡马克方案的呼声日渐高涨,尤其是负担了45%建造费用的欧洲。“要是我们真的想把这笔钱用来拯救地球气候、摆脱能源危机的话,选择ITER这个项目显然就是个笑话,”欧洲议会绿党的能源顾问米歇尔· 拉凯(MichelRaquet)如是说。欧盟目前正考虑给ITER一笔约为27亿欧元的经费,好让这个项目能按预期在2020年之前完成建造。作为ITER在欧洲最主要的反对者,绿党担心这将让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丧失很多研究机会。
美国只负担整个费用的9%,所以反对的声音较弱。用托马斯· 科克伦(Thomas Cochran)的话来说,ITER“不构成一种威胁,只是浪费钱财而已”,身为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旗下的一名反核斗士,科克伦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反对那些会带来长期污染,或能加速核武器制造技术传播的核研究计划上。美国国会对ITER的态度似有不同,作为积极鼓动核聚变研究的美国聚变能源协会的会长,史蒂芬·迪安(Stephen Dean)认为,“只能说目前没有要中止这个项目的迹象”。但事无一定,今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缩减美国国内核聚变研究经费的同时,大幅增加了对ITER的投入,但即便这笔经费如期到位,也只有1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应承担的设计预算的25%。其他国家在履行对ITER的承诺时,也碰到了一些麻烦。印度正费力地推销着手中的合同,而去年3月,大地震破坏了日本的一些关键工厂。俄罗斯驻ITER代表弗拉基米尔· 弗拉先科夫(Vladimir Vlasenkov)形容目前的情况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拖延的理由”,说完他立马加上一句,“俄罗斯那边一切正常”。
ITER能检验核聚变是否可行,但它不能证明核聚变是否能商业化运行。反过来,我们倒有很多理由说明后者不可行,最简单的理由就是聚变过程中的辐射强度非常高,能损坏象钢这样的普通物质,因此核聚变电站需要采用一些目前还没有的新材料,才能抵挡等离子体长达数年的轰击,不然反应堆就需要经常停机检修。再者,燃料氚的来源也成问题,发电站必须自行制备,比如利用反应堆本身的核反应过程来制造氚。
有人认为,建造一台基于ITER技术的反应堆,最大的障碍在于该装置极端的复杂性。那些特殊的加热系统和自制部件可能在实验中运行良好,但作为电站需要的是简单、易维护,国原子能管理局总裁史蒂夫· 考利(Steve Cowley)说,“无法想象一台到处叮叮咣咣的机器怎么能日复一日稳定工作”。 因此,在并网发电之前,还必须建造第二代的验证性反应堆——不用说,同样造价不菲。考虑到目前ITER跌跌撞撞的前进脚步,在本世纪中叶之前,什么也运行不起来。
尽管核聚变能源整体发展存在着这些阻碍和不确定因素,但熟悉ITER的人都认为,该项目势在必行,竞争压力是原因之一。“法国看到美国参加,他也肯定要参加;美国不退出,他也不会退出,”科克伦解释道。从律师的角度来看,图伊德认为,如果各个参与国提前退出,可能导致在未来无法获得一些新技术,这也将促使该项目继续运行。
即使抛开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谈,很多科学家内心里都觉核聚变是满足世界能源需求的唯一希望。美国重返ITER时,雷蒙德· 奥巴赫(Raymond Orbach)刚好是美国能源部的首席科学家,他说自己“对世界未来的能源需求感到惊恐,到时候从哪弄这么多能源?核聚变不会释放二氧化碳,基本上取之不竭,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你还能找到第二个么?” 大多数核聚变科学家都认为,全球气候剧变不可避免,等到时过境迁,人类终尝苦果之日,“我们最好已经准备好了应变之策”, 这是考利的告诫。秉持此念,终将得偿所愿,因为我们已背水一战。
| ![]()